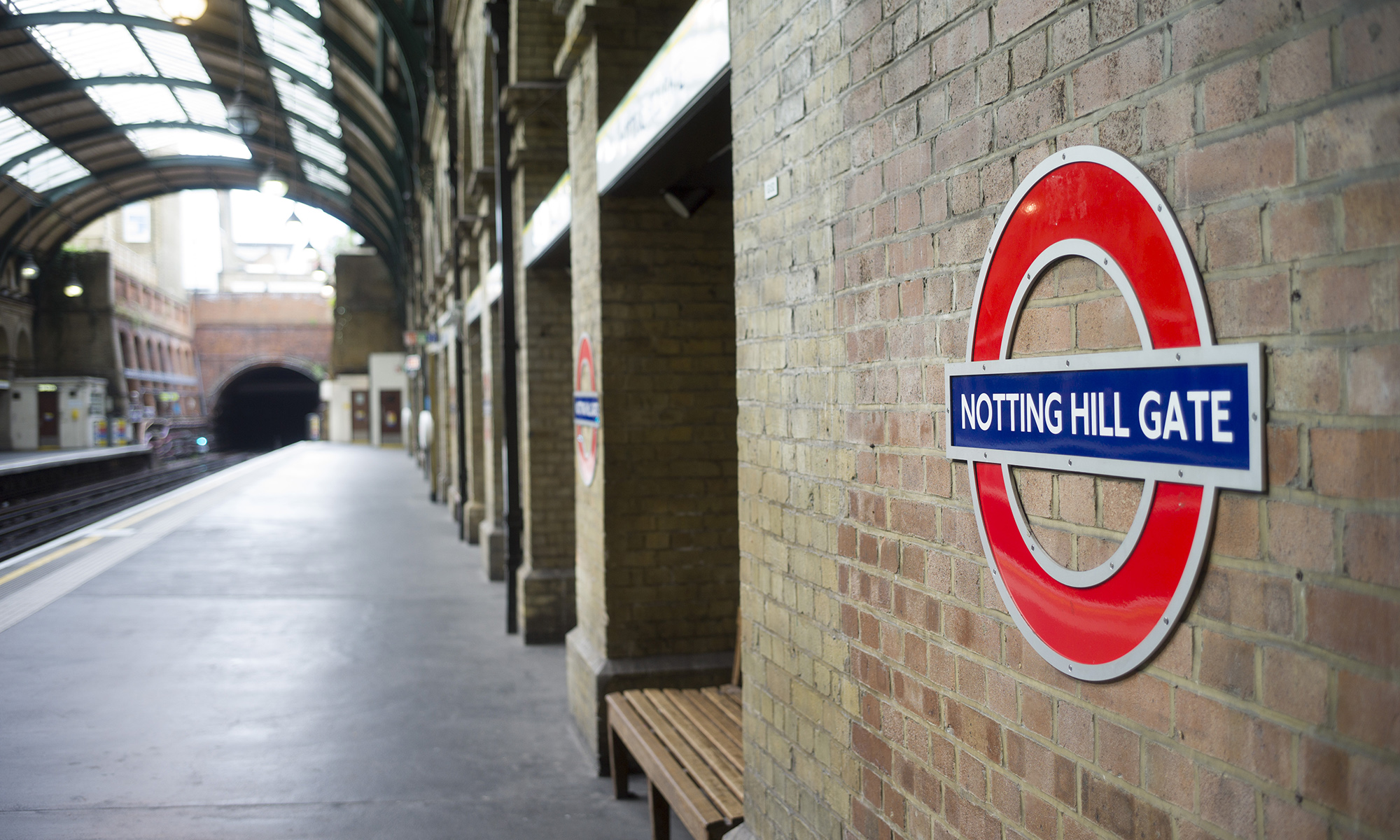中國人有一個奇怪的嗜好,就是喜歡講原意。文人在千多年前寫的詩詞,我們都喜歡追究其生平際遇,看看字裡行間會不會隱含一些憤世嫉俗的『原意』。在錢鍾書的《圍城》裡,他便對此打了一個幽默的比喻,謂當你覺得一隻雞蛋好吃的時候,為什麼要考究那隻生下它的母雞?石堅叔幾十年來演過不少歹角,難道這又跟他的生平際遇有關?
早前吳光正在《明報》批評李柱銘對《中英聯合聲明》斷章取義,把原文『… 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,50年不變…』中『原有的』刻意刪去。為此,李議員也投搞伸辨﹝見明報的《均衡參與非為保障免費政治午餐》﹞,其中一項提到『保持原有』並不等於原地踏步。社會不斷地改進,《中英聯合聲明》在 1984 年簽訂時候,不能預見,也不能限制往後六十三年裡的政制發展。再者,要是原意真的要保持『原有』的制度的話,那末基本法中的『循序漸進』地發展普選豈非自相矛盾?
原意真的重要嗎?原意真的切合現實需要嗎?在《走向共和》一劇的慈禧太后便經常把『咱們不能壞了祖宗的規舉』帶在嘴邊,弄至朝廷腐敗,直接影響了清朝的滅亡。借假諷今,連從前的鄧小平也鼓吹經濟改革,今天卻竟然還有人要追溯原意,政制倒退回二十年前鄧主席的思維,要是他泉下有知,難保不會氣得復活過來。
香港人都是進取的,不會頑固的死抱著原意,因為我們都明白到過去不能解決現在的問題。
- 兩口子走在一起時原意是為了快樂,但他口臭大男人不求上住,她斤斤計較絮絮叨叨無理取鬧,兩人整天吵吵鬧鬧,原意可以幫得他們多少?
- 董特首原意是要搞好香港,八萬五計畫原意是要降低樓價,務求『居者有其屋』,現在呢?
- 木尺原意是要來量度長度,卻常常被老爸拿來『教仔』。
- 夜壺原意是要與人方便,現在卻成了古董家的收藏品,現在誰還會撒泡尿進去?
- 小女孩趁父母外遊之際,買了一套老翻《無間道》回家跟男朋友小聚二人世界,誰不知裡頭放的卻是《咸濕媬姆賤嬰兒》。這一夜,翻雲覆雨,兩人像交了惡的秀才般溫柔地廝殺,情與慾在三合土機裡混得化不開,原意早被攻佔得體無完膚,兩小無猜,他們才沒空去談論這個問題。
24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