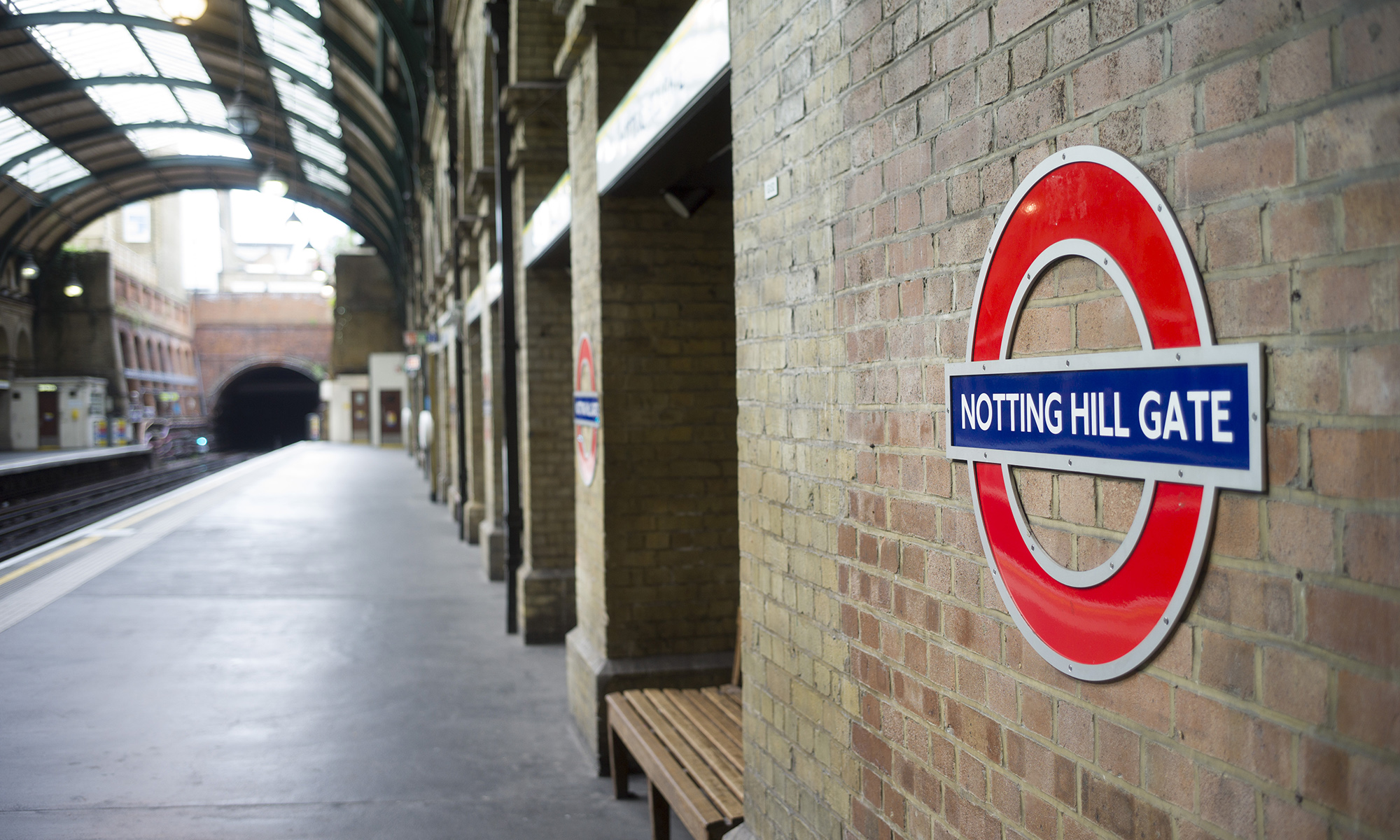最近看了《豪情》這部電影,算不上是自己喜歡的一部戲,但難得的是劇本寫得完整,不像二流港產片般粗糙堆砌,屬於用心的作品。以片中的兩段感情為例,故事大綱寫古天樂及陳奕迅各自擁有一段美滿的感情生活,後來因『工作』關係而移情別戀。劇中兩位男主角都是聰明能幹的大學畢業生,背後的兩個女人﹝何韻詩及應采兒﹞同樣是有情有義、善解人意、漂麗慧黠的女孩子。在兩段近乎完美的組合下,要加插兩個風塵女子來介入,劇本的難度可謂相當高。三流的劇作家大概會安排一段矇矇矓矓的一見鍾情戲,再加一個男主角神魂顛倒、目瞪口呆的鏡頭,胡胡混混地敷衍了事,觀眾都成了騙局裡的羊牯。
《豪情》的故事,編劇或多或少希望表達他對現實社會的看法,所以劇情必須要令人信服。故事首先描寫陳奕迅是一個單純的青年人,當遇上『技術』了得的何超儀後,便迷上了這種低俗的歡愉,導致女朋友離去。後來浪子回頭了,重回何韻詩的懷抱,這令我想起多年前的新聞人物陳健康先生,在人物性格及際遇上都有異曲同弓之處。相比陳奕迅,古天樂的角色比較理性,最後能令古天樂著迷的是令人模不透的周麗淇,大概是一種如酒般愈釀愈醇的感覺,跟何超儀可謂兩個極端,該特點早在夜店猜枚時已經表現得一清二楚。
最近有網友跟我討論美與藝術之間的關係,簡單一點說,表面上的美是否等於藝術的美?許多朋友的答案都是肯定的。然而,藝術所包含的領域並不局限於視覺,而是更超然地,是作者與欣賞者之間的感情交流,這種感覺不能言喻,只能夠矇矇矓矓地從作品中意會出來。所以一幅相 sharp、一篇小說文采華麗、一幅畫畫得真,若然缺乏了作者的感情交流,都不能算藝術。
要了解藝術的美與表面美其實不難,就像《豪情》裡四位女主角的分別一樣。何韻詩、應采兒、何超儀及周麗淇都美麗,但前兩者所扮演的角色都只屬於一種凡俗的美,單純地溫柔、體貼、標緻,統統流於表面上的條件。當周麗淇出現後,她就像蒙羅麗莎的微笑一樣,給古天樂一種似笑、非笑、捉摸不定的神秘感。假如應采兒是一壺清茶,周麗淇就是一瓶醇酒,予人愈飲愈醉、愈飲愈著迷的感覺,這就是藝術。
每位藝術家在初打開藝術之門的時候,很容易會走入了『快感』的歧途。朱光潛博士在一篇《希臘女神的雕像和血色鮮麗的英國姑娘》對美感與快感有如下解釋:
『… 從我們的立腳點看,美感和快感是很容易分別的。美感與實用活動無關,而快感則起於實際要求的滿足。口渴時要喝水,喝了水就覺到快慰;腹肌時要吃飯, 吃了飯也就覺到快感。喝美酒所得的快感由於味感得到所需要的刺激,和飽食、暖衣的快感同為實用的,並不是起於『無所為而為』的形相的觀賞。至於看血色鮮麗的姑娘,可以美感也可以不生美感。如果你覺得她是可愛的,給你做妻子你還不討厭她,你所謂「美」就是祗合於滿足性慾需要的條件,「美」就祗是指對於異性有引誘力的女子。如果你見了她不起性慾衝動,祗把她當作線紋勻稱的形相看,那就和欣賞雕或畫像一樣了。美感的態度不帶意志,所以不帶佔有慾。在實際上性慾本能是一個最強烈的本能,看血色鮮麗的姑娘而能『心如枯井』的不動,祗一味欣賞曲線美,是一般人所難能的。所以就美感說,羅斯鏗稱金的血色鮮麗的英國姑娘對於實際人生距離太近,不一定比希臘女神雕像的價值高。…』
快感跟美感同樣都是感覺,但前者只是為了『實際要求的滿足』而提煉出來的低俗情慾,跟藝術不可混為一談。《豪情》中的何超儀就是這類型的角色。
33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