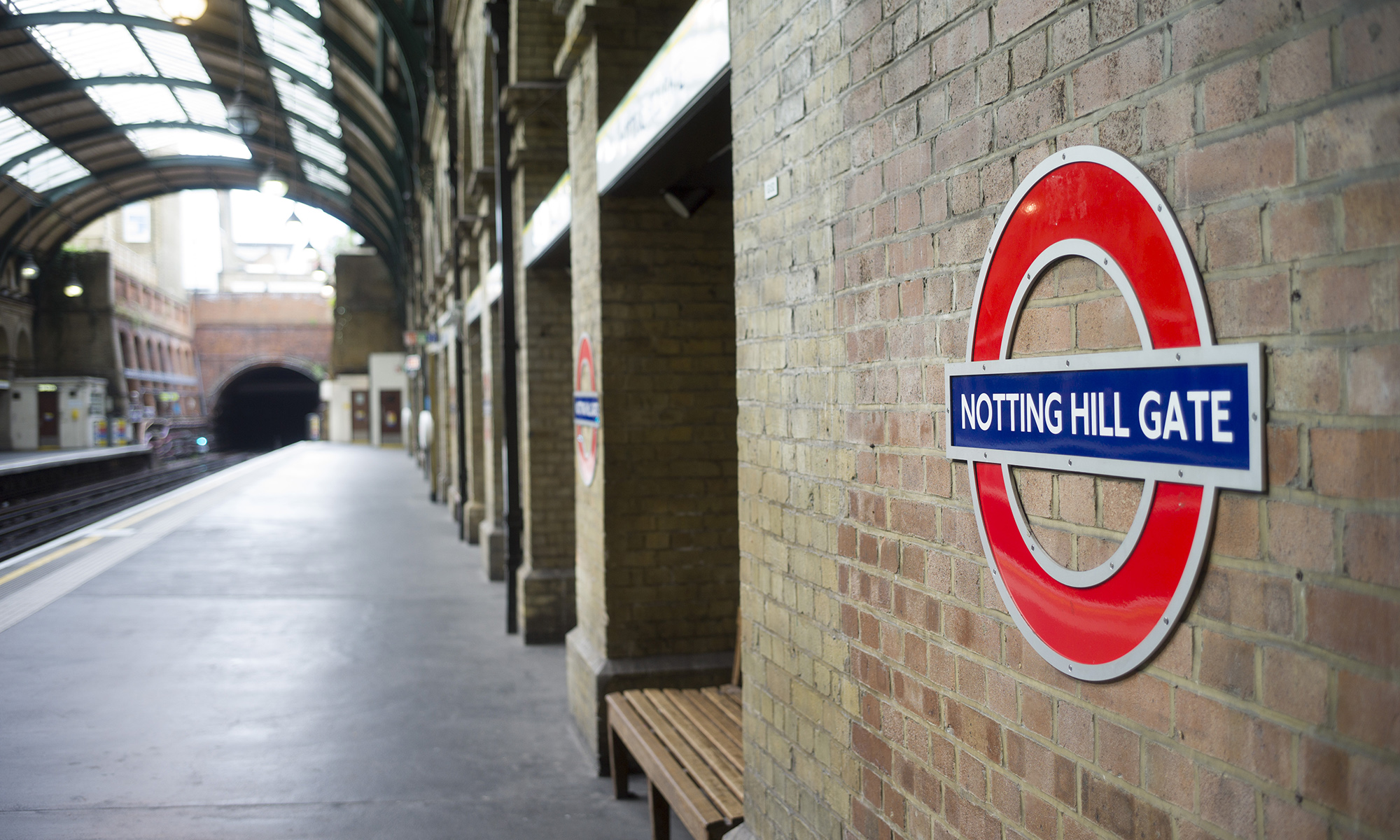風險管理﹝Risk Management﹞是一門很廣泛的學問,工商管理、保險、金融投資、營運、工業工程﹝Industrial Engineering﹞、軟件工程﹝Software Engineering﹞等等都包含風險管理。顧名思義,風險管理就是在作某項決策之前,先作風險評估,再衡量自己的風險承擔能力,又或者想辦法降低風險。以股票投資為例,風險評估就是先對公司作資產評估﹝Equity Research﹞及分析,而分散投資或購買基金等等都是降低風險的其中辦法。總而言之,香港師奶買股票先挑一個號碼,再買其升跌,都是缺乏風險管理常識的投資,跟賭博無異。
近日有一則令人不快的新聞,父親獨留四歲兒子在家,因未有把窗花鎖好而釀成了意外,這又是另一個缺乏風險管理常識的典型例子。小兒子熟睡、只離開短時間、兒子房間的窗花已鎖上,雖然種種環境因素已經把風險降低了,但並非萬無一失。問題是意外發生的後果能否承擔得起?香港人一般都有『過左海就係神仙』的賭博心態,把兒子獨留在家,『冇事o既』;十分鐘後返家,發覺兒子安然無恙;『都話冇事o架喇』,投機險勝,中間的過程其實就是『博』﹝意謂『賭博』的『博』﹞。
生命裡不能『博』或不值得『博』的東西多的是,只是人類都是犯賤的動物,正所謂『唔見棺材唔流眼淚』。在闖禍之前,我們都缺乏警覺,盜竊、帶翻版貨過關、用不合規格的電器﹝例如內地製造的水貨電器﹞、亂過馬路、醉酒駕駛、諱疾忌醫、防煙門長開等等都是隨手拈來的例子。『博』的原因不外乎是因為低估了風險,或甚漠視了風險的存在,是二而一,一而二 ── 蠢。
最近在看鳳凰衛視的《唐人街》,其中一集說到兩位內地婦人在互聯網上認識了現任的丈夫,不約而同地飄洋過海,嫁到彼岸的美國去,導演的結論是 ── 其實她們都不快樂。我一直都不認同『網戀』﹝見《瞎了眼睛的女人》﹞,並非說互聯網內找不到好男人,只是透過營光屏去了解一個人實在太困難。他誠實嗎?還是選擇性地誠實?除此之外,習慣、價值觀、性格、脾氣、嗜好、品味、背景、口臭、紋身等等,我們能夠認識的部分實在太少,模糊的只能有作個美麗的假設,這都是『博』的戀愛心態。神仙過不了海,後果承擔起嗎?這是一個誰都懂,但誰都會犯的錯誤,並非表示所有網中人都缺乏戒心,只是當愛情降到頭上以後,人總會變得愚昧罷了。
243